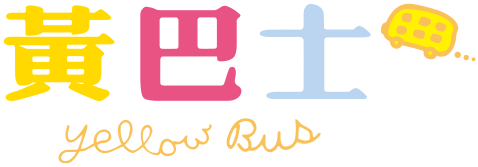朱鳳嫻有一對視障父母,她曾經以為父母帶她來到這個世界,只是私心地希望有個人能當他們的眼睛,更曾一度想掙脫這個不完美家庭的枷鎖。直至她將父母的故事拍成電影《一路瞳行》,才從媽媽口中知道真相:「很多人質疑我為甚麼要生小朋友,那是因為我想帶她來看看,一同感受這個世界有多美好。」
與父母的關係是內心的痛處
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的朱鳳嫻主修表演,畢業後十年都是自由身藝術工作者,一直演繹別人的劇本和故事。十年過去,她發現自己也有想講的故事,於是毅然轉向劇本創作發展。二零一一年,她創作的流行小說《我的援交日記》受到電影公司青睞,希望拍成電影,她自薦做電影的編劇,劇本最終被拍成電影《販賣.愛》。隨後她用外婆的真實故事寫成舞台劇劇本《失禮.死人》,劇本入圍「二零一四台北金馬影展──金馬創投會議」,勇奪「Moneff Award」,並獲得第二十五屆香港舞台劇獎提名「最佳劇本」,成功鋪墊出她的編劇之路。
《一路瞳行》是關於她和父母的故事,觸及她內心深處一些從未吐露的情感。這部劇本她認真花了十年時間琢磨,期間曾以舞台劇的讀者劇場形式,以及一部她親自執導拍攝、並由她父母作本色演出的十五分鐘短片,來收集觀眾的反饋。「我本想用這個故事抒發自己的內心感受,意想不到的是,觀眾都把焦點放在我父母身上。他們認為父母照顧我時必定遇上很多困難,我卻從未試過站在外人角度看我們這個家庭的生活有多麼不簡單。觀眾的反應讓我知道,假如電影能呈現更多我父母的生活面貌和態度,相信可以鼓勵和溫暖不少人心。」朱鳳嫻拿着《一路瞳行》這個故事逐家逐戶去叩電影公司的門,最終獲得東方影業支持,二零二零年開鏡拍攝,並於今年九月上映。
不一樣的童年
父母都是失明人士,一般人必然先入為主,以為朱鳳嫻一家活得很淒涼,要靠政府接濟才能過日子。其實她爸爸有工作足以養活一家三口,唯獨她的童年確實過得比別人不一樣。「我小時候很少去公園玩,因為父母眼睛看不到,他們不是怕我自己跑開,而是擔心我被人拐走。不能去公園玩,爸爸於是在家用木板自製了一條滑梯給我,將表面打磨光滑,就掛在碌架床上讓我玩,不夠滑的時候他會倒一點爽身粉,我很記得我玩得很開心。」現今一般父母喜愛用影像或者短片去記錄孩子成長,朱鳳嫻的成長卻鮮有相片,因為父母根本拍不到,唯有親友帶相機來作客時才有機會影幾張。「媽媽記錄我成長的方式是靠一部小小的錄音機,例如錄下我第一句說的話,並會在吃飯時播放錄音讓全家一同回味。」
小時候的朱鳳嫻和父母很親近,她每年的生日願望就是祈願父母的眼睛能夠重見光明;又經常會為父母受人白眼而替他們「出頭」:「試過搭升降機遇上小朋友問爸媽,為甚麼我父母的雙眼會這樣,身旁的大人竟然答他:『因為他們看電視看太多了!你千萬別看太多,否則就會跟他們一樣!』這樣令我很不高興,但我只能惡狠狠地瞪着他們,以表憤怒。我的父母卻完全沒有為此而生氣,媽媽說:『不用管別人說甚麼,你知道事實就夠,不用介懷,我們不痛也不癢。』」朱鳳嫻形容母親是智慧老人,父親是幽默大師。媽媽總能以睿智和強大的內心面對和解決各種生活上的困難,爸爸則是家庭的快樂調劑品。外人看這個家庭,總以為是女兒照顧父母,事實是朱鳳嫻由父母悉心照顧長大,特別在她初生和童年時期,父母需要克服的困難實在不足為外人道。
失明父母的育兒日常
朱鳳嫻的雙親都是因為小時候生病發燒致盲,兩個人都在大約三、四歲時失去視力,因此身體孱弱的女兒每次發燒都令他們特別憂心:「有次發燒,父母緊張地抱着我老遠跑去旺角看相熟的家庭醫生。八十年代仍未有很多輔助失明人士的設施,例如過馬路的響鬧提示,爸媽日常只對自己每日必須往來的街道熟悉,例如我的幼稚園、街市和工作地點,其他地方很少會去,能夠自己搭車去到旺角已經很了不起,回來還要給我餵藥。他們會用橡筋來標示吃藥的份量,媽媽日常亦會將所有東西放得井井有條,確保不會拿錯。」

因為拍攝《一路瞳行》,媽媽亦告訴了朱鳳嫻一件她從未聽過的往事。「小時候媽媽把我放在自行車上,她在廚房切菜,忽然聽到客廳傳來正在煲粥的電飯煲從雪櫃頂翻倒在地上的巨響,原來在學行車上的我不小心拉到電飯煲的電線。媽媽出來時被滿地熱粥跣倒了,其時家裏一片死寂,良久我才發出喊聲。幸好我沒有被熱粥正面淋到,只受了輕傷,媽媽卻心痛地表示:『如果妳被熱粥淋到留下疤痕,我也不知怎算好!』媽媽多年來一直不願意提起,是因為心裏仍猶有餘悸,到今天依然責備自己不夠小心。」失明父母育兒階段需要面對的困難和壓力,其實跟一般父母無異,同樣需要憂心子女患病、跌倒或者受傷,但他們比一般人需要更多智慧和耐性,去解決生活上各種各樣的困難,讓他們不必依賴他人,自己一手一腳照顧好孩子。多年後朱鳳嫻才理解到,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,其實需要互換位置去互相諒解。

反覆的母女關係
女性縝密的心思和某些不易吐露的情感,令母親與女兒的關係總是比較複雜和糾結。朱鳳嫻與媽媽的關係在她升中後急
轉直下,踏入青春期的她與渴望理解女兒內心世界的母親發生衝突。「因為媽媽眼睛看不到,從我讀幼稚園開始,都會在我出門前從頭到腳仔細摸我一遍,檢查我的儀容是否齊整。小時候覺得很習慣,中學開始卻變得很抗拒,媽媽會檢查我有沒有釘耳洞和穿短裙等,令我感覺像坐監一樣。」朱鳳嫻不單止越來越抗拒分享自己的心事,更因反叛心理作祟,曾對媽媽說過很多難聽的說話,微細的衝突累積導致母女關係變得越發緊張。
《一路瞳行》亦有拍出這真實的一節:媽媽來到校門前找女兒,電光火石間,女兒要在同學和媽媽之間作出選擇,當時很介意被同學知道自己有一對失明父母的她,選擇背向母親而去。「父母能完全接受自己失明,我卻礙於自卑和保護自我形象,很想把這個家庭背景藏起來。當時屬於青少年自我形象建立的時期,我沒有勇氣去打破自己的形象。」眼盲卻心如明鏡,媽媽知道女兒不認她,卻把眼淚往肚裏吞,從沒表現出傷心失望之情。即使朱鳳嫻往後曾試過離家出走,媽媽永遠也是第一個先軟化下來,主動去找她,甚至先說對不起的人。「媽媽的偉大之處是不會生你一輩子的氣,縱然傷心失望,但她始終會選擇原諒。」朱鳳嫻懺悔昔日將自己放得太大,以為自己是家中有眼睛的一位就比較優越,忘記看到父母的能力,「自我膨脹令我看不到他們的付出。」
雖然間中水溝油,但知女者莫若母,媽媽的智慧之言與精神上的無限支持,成就了今天的朱鳳嫻。「父母知道我喜歡畫畫和表演,就鼓勵我去試考演藝學院,我卻心大心細又怕失敗。媽媽反而是個勇於嘗試的人,她去過台灣跑馬拉松,又會去游水,她認為人生應該甚麼都嘗試,試過才知道是否適合自己。很記得她對我說:『既然做甚麼都會辛苦,當然要選一件自己喜歡的工作去做,好過為了賺錢迫着做不喜歡的事。』」朱鳳嫻最感恩的是媽媽從來沒有將世俗的標準套用在她身上,並對她百般信任和鼓勵:「他們是視障人士,自己亦未必達到社會一些標準,因此他們也沒有用社會標準去規範和要求我。她從來只教我核心的做人道理,一些成長必學同時畢生受用的價值,而非學術和技巧上的東西。

創作是一個自我療癒與和解的過程,朱鳳嫻為拍攝《一路瞳行》,將過去的自己活生生剖開,坦白地承認自己曾希望拋下雙親遠走高飛,渴望擁抱自由和自主人生。直至四、五年前發現父親患癌,她才意識到原來陪伴雙親的時間如此有限,父母不會永遠在原地等你,爸爸最終在電影開鏡前離世。朱鳳嫻坦言:「很多人跟我一樣忽略了家庭,會對家人特別缺乏耐性,計較自己的付出。今天我才明白,人生裏很多東西可以選擇,唯獨家人是不能割捨的。哪怕大家鬧到面紅耳熱,即使有些價值觀不同,他們依然是你的家人,這是不能改變的事實。從前我以為割捨了雙親便可以過自己的新生活,但其實我整個人生都充滿着我原生家庭的影子,唯有解開原生家庭這些結,唯有家庭這個永遠在背後、令人安心的避風港,才可以令我們有勇氣走得更遠。」即使這個家並不完美,闖蕩過後朱鳳嫻最想的,還是回家。